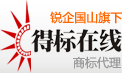法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是政治家、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所有法律职业者的共同追求,我们所有的奋斗,就是要实现一个法治的世界,一个和谐的世界[①]。实践这一伟大目标,基层司法面临着诸多现实艰难与困惑,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沉重话题。
一、基层司法的现实冲突与矛盾
1、诉讼案件飙升与法治信仰的淡漠。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每年的民事的案件平均只有50多万件,而20年后则上升到了500多万件,是上个世纪末的10倍[②]。解决社会纠份的机制和方式是多元的,近年来社会大调解的矛盾调处机制的建立,并未以根本上减轻基层法院受理案件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北京朝阳区法院2000年到2005年,收案几乎翻了一倍,2005年,全院在编人员只有340多人,收案数却已超过50000件[③]。诉讼案件的持续走高,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一方面,对基层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当事人自觉履行率和法院强制执行率极低;另一方面,当事人对基层法院裁判的案件,无理缠诉缠讼,涉诉涉法信访案件居高不下,2005年上半年,山东每月来省、赴京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达432件,其中,平均每天会出现3至10名无理缠访者[4],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全国法院处理涉诉涉访58.3万件(人)次,而提起再审的仅67852件,审结63965件,依法改判的21410件,提起再审率和再审改判率仅为11.7%和33.5%,信“访”不信“法”的心理体现的是当事人“法大于权”的“人治”观念。近年来,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活动中侮辱、谩骂、围攻、殴打审判人员等妨碍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现象时有发生。[5]
2、法官素质不高与法官员额的缺失。从法律人的视角评价基层法官职业化程度、素质和行业形象不高似乎已成为不争的现实,媒体频频报道的“三盲”院长姚晓红等“负面”人物,更是给基层法官群体刻下了深深的污痕。最高法院连续多年已各种方式和内容的教育、整改活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基层法官违法违纪问题。最高法院近年来很少公布过查处违法违纪法官的具体数字,取而代之以百分比,如“2004年,全国法院违法违纪法官人数比2003年下降42.74%”;“全国法院违法违纪人数已从1998年6.7‰下降到2002年的2‰”,[6]徇私枉法、吃请受贿已成为较为普遍的“顽症”。专家和学者强烈呼唤的法官职业化、精英化改革,在基层法院收到的成效也仅仅是提高了法官的职业门槛,一些消极散漫、言行轻浮、敷衍塞责、社会和公众评价极低的基层法官很难清退。与此同时,法官的流失[7]、缺额现象非常严重,与人民法院在国家体制中的崇高地位相比,法官职业还仅仅是从业人员养家糊口的生存需要。在一些较为贫穷、落后、闭塞的西部地区不少极具潜力和才华的年轻法官迫于生活、工作条件的艰苦、较低的工作待遇,纷纷离开所钟爱的审判岗位,肖扬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也坦陈:“中西部地区法官队伍人才流失严重”,基层法官后继乏人的状况已经显现出来,且已影响到基层法院审判正常运转[8]。但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状,显然需要漫长的过程。
3、规范司法行为的整改与背离审判规律的运作。按照中央政法委和最高法院的部署,全国法院深入开展了“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事专项整改活动。根据最高法院检查组对20个省区的检查结果表明,通过专项整改活动,“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反映的一些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规范管理的工作局面初步形成,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形象得到进一步树立,各项审判和执行工作得到全面发展[9]。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改活动并未改变实际工作中基层法院参与行政、背离司法职能的运作。基层法院审判工作泛行政化的问题,由来已久,取消农业税之前,不少基层法院参与了催缴税费、计划生育突击等活动,此后又参与了地方招商引资、政府征地、拆迁等,令人匪夷所思,严格说来,法官不仅没有义务承担这些事务,而且从法律上看是不应该甚至应当禁止的。无论依照什么诉讼或传统的法理,法官们的这种做法都是与司法的职业道德有冲突的。[10]
二、基层司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应对
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而司法是基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司法现实艰难和所面临的尴尬,有待从体制和制度上通过改革和创新加以解决。另一方面,立足国情和实际,努力提高基层司法能力,更好地发挥审判职能,不断推进法治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更加全面、充分、有力的司法保障则也是当务之急,不容忽视。
1、强化法治理念下基层法院的大局意识。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其职能是审判刑事、民事、商事、行政诉讼案件。强化法治理念下基层法院的大局意识,首先就要确保基层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院的审判活动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接受法律的监督,但不能听任何人的指挥和摆布、超越审判权限。司法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彰显的自身独特价值和司法本性应当受到尊重,司法的功能勿庸置疑,司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并非是一味包治社会纠纷百病的“灵丹妙药”。
在这方面,基层法院的院长肩负着沉重的压力和重要责任。在现实的司法环境和条件下,要坚持做到在权势而前始终保持对法治的信仰、忠诚、不趋炎附势,才是法律人的品性,法治每向前推进一步,和谐社会的美好未来社会离我们更近一分。其次,强调“法治” 理念,就要遵循司法规律,规范司法行为。司法为民是新时期人民法院的工作宗旨,要求人民法院在从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中,心中装有群众,时时想着群众。通过制度的完善、程序的规范,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充分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力[11]。而不是把它做为一句简单的口号或商标,把一切司法活动都以之冠名,为了司法为民,标新立异,生造出五花八门的改革,这无疑是曲解了司法为民的思想内涵和实践意义。
强调法治理念下基层法院的大局观,不是要基层法院走封闭自我的职业之路,而是要通过司法民主的方式,体现人民司法本质,围绕发展和稳定的两大主体,通过审理和执行案件,解决纷争,调节和维护社会基本秩序,谋求社会的和谐发展。
2、强化基层法官司法能力建设。基层司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体现在具体个案审理和执行过程中。取决于基层法官司法能力的强弱。对正义的实现而言,操作法律的人的质量比其操作法律的内容更为重要[12]。强化基层法官司法能力建设,既有现代司法理念、职业道德和意识、职业技能的全面要求,也要结合实践突出重点。
强化基层法官准确适用法律的能力,这是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基层法官处在审判工作的最前沿,无论是法官数量还是办案数量,基层法院都占80%左右的比例,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纠纷案件的一审,基层法院在审判中凭借对法律的准确理解和把握,选择法律适用于具体个案作为裁判规范,是维系司法公正最为核心的工作,也是法官裁判案件的基本功,在我们这个本土文化缺少法制传统的社会,各种类型的矛盾纠纷,其具体表现形式迥异,存在法律漏洞不可避免,机械、单纯的工匠式的基层法官难以胜任其职,当法律没有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即使不拒绝对当事人的纠纷作出裁判,这样的法官也会束手无策,如卡多佐担任法官的最初几年,“发现在我航行的大海上没有任何航迹,为此,我烦恼不已,因为我所寻求的是确定性,当我发现这种追求徒劳无益时,我感到万分压抑和沮丧[13]。而对各种新类型和千奇百怪的纠纷作出公正裁判,则需要弥补法律所固有的缺陷和漏洞,体现基层法官对法律精神、法律原则的理解和法学理论功底的素质,折射出法律智慧的光芒[14]。
要强化基层法官平息纷争的能力,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需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大量由于社会变革,经济结构调整而导致不同利益深层次纠纷大量涌入到基层法院,维护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要完成有效解决纷争的重任,不仅要做到司法的公平正义,而且要定纷止争,案结事了。通过司法所独特的语言、道德、知识、经验和要求,做好诉讼各方当事人的工作,清除当事人之间尖锐对立的情绪,通过辩法析理,说明教育,化解当事人之间的隔阂,妥善解决矛盾。要提高案件的调解能力,发挥人民调解和人民陪审员的作用。适用各种调解手段和调解方法,消弥对抗,平衡利益,化干戈为玉帛,实现法律效果和办案效果的有机统一。要提高处置复杂局面、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对审判和执行适程中可能发生的当事人“抢亲”、报复、自杀自残、故意毁损财物、哄闹法庭、伤害、威胁以及极端方式要挟法官的暴力抗法事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超前工作加强防范,尽可能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难以防范的突发性事件,更是要沉着冷静,及时控制住局面,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和激化,妥善应对。
3、强化基层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正如中国的法治化一样中国法官的职业化,也是历史渐进的过程,在现有条件下,一方面要在基层法官中大力倡导和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塑造一支能承受住各种压力和艰苦考验、矢志不渝为人民审判事业无私奉献的基层法官队伍;另一方面,强化法官的职业保障,加快对法官待遇的各项落实,根据《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规定,法官的薪金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以与他的地位、尊严、职务、责任相适应。较高的待遇不一定保证司法廉洁,但待遇不高一定不能保障司法廉洁,法官应当获得高薪[15]。
要进一步完善基层法官的教育培训,建立了强有力的教育培训机制,对基层法官实行强制培训,是提高基层法官素质的迫切需要。如果法官素质低下或缺少培训,就会造成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反复无常,或者对事实的认定扭曲,那么法治就不会发挥如此作用。……聪明但腐败的法官可以造成危害,诚实却无能的法官也同样可以造成危害,而后者则更可所,因为只要他审理案件就会有危险[16]。独立的法官如果不是司法裁判领域的专家,就可能造成人为的司法不公;而且只有形成裁判者的职业化,才有可能在法官之中形成特有的职业传统;而这种职业传统反过来又会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确保法官阶层具有抵御外界干预的勇气和能力[17]。
采取多种形式,解决中西部法官缺额。建立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经济欠(不)发达地区基层法官的交流制度。一是从发达地区法官数量较多,案件相对较少的基层法院抽调一部分法官支援中西部地区基层法院工作2—4年,以帮助其解决法官员额不足的问题;二是实行对口帮扶制度,由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基层法院和中西部的基层法院定点挂钩,结成帮扶共建对子;三是对中、高级法院中拟选拔任用而又缺乏基层法院工作经历的法官,实行到中西部基层法院工作二年以上制度。相信在法院内部坚持数年,对解决基层法院法官员额不足、素质不高的问题会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