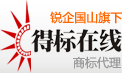小时候,家里的许多铁器,诸如割稻的镰刀,劈柴的斧头,锄草的锄头,切菜的菜刀,裁剪的剪子……都是由铁匠用锤子一下一下锻造出来。
打铁是男人的事业。这是因为,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没有吃苦精神不愿打铁。我国有句俗语:“打铁先要身板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每至烘炉生火之时,都是温度骤升,拉一阵风箱,可汗水满头,抡一番铁锤,便会挥汗如注。那十几斤重的大锤抡番起落,需要超人的力量与气度。
有时打铁真的好像一支交响曲。风箱拉起,曲子奏响。随着加热的需要,那风箱会在平缓均称的节奏中加速,强力的节拍中充满希望。那炉中的火苗,一起随风箱的节拍跳跃,在劲风的吹奏中升腾。待铁器热至彤红,铁铗快速夹至大铁墩上,一番铁锤上下,一串钉铛声响,一阵汗雨飘下,那铁件便成为匠者的理想器物。有时需要,师傅会把铁器放入水槽内,随着“吱啦”一声,一阵白烟倏然飘起,淬火完成。打铁的奥秘便是“淬火”。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因此,为了使铁器坚韧锋利,“淬火”这道工序就是一个难度大,技术性极强的活儿。在何时把铁器放入水里,在水里浸泡多久,这些都是铁匠必须把握的。一旦淬火“老”了,铁器就失去了刚韧,用起来费力不讨好;一旦淬火“嫩”了,铁器虽锋利但易损坏,但怎样才能恰倒好处,这便是铁匠的真经了。
近年来,铁匠的生意渐渐地清淡了,好多都放弃了自己的手艺而出门远行。方圆几十里,我所熟悉的铁匠,只有王铁匠依然在自家门前保留着那简易的铺子。坚守着那块古老的手艺活阵地。
王铁匠的镰刀在我们那里远近闻名,是家乡一绝,镰刀上专门有“王”字记号,就像现在一些产品的商标一样驰名,夏天收割时节得提前预定,否则无法保证。那镰刀不大不小、钢材不薄不厚,握在手中轻巧,割起稻子来利索,且钢刃好,耐磨。磨刀石轻轻一磨,就会再次焕发活力。
王铁匠干着硬朗朗的活儿,做着实实在在的事情,靠力气吃饭,凭本事挣钱。他所具有的,正是我们所缺乏的。